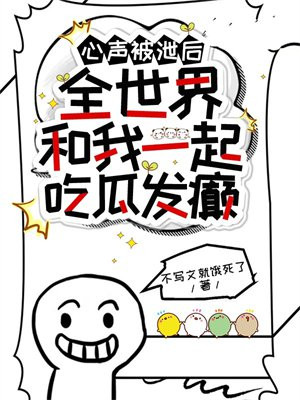V·S·奈保尔提示您:看后求收藏(宜小说jmvip5.com),接着再看更方便。
他们来到起居室。透过房间一角一扇敞开的门,威利能够看到厨房里,一个女人正坐在水磨石地板上,手在一个盆子里揉捏着什么。还有两扇门通往里面的房间,也许是卧室。
威利还看见起居室里有一张沙发或者是小床,铺着床单。约瑟夫小心翼翼地在床上躺下,这时候威利才发现约瑟夫身有残疾。床底下,床单后面,隐约可以看见一把夜壶的手柄,而就在约瑟夫的枕头下方,放着一只焊了锡把手的锡杯,或许早先是炼乳罐子——那是他的痰盂。
约瑟夫或许看出了威利脸上的哀伤,于是他重又起身,站在威利面前。他说:“我可不像看起来那么糟。你看,我能站起来走动。但是我一天只能走大概一百码。不算多。所以我不得不小心分配我的精力,即使是在这里,在我们大学的住宅区里。当然,如果有一辆车、一台轮椅,就有可能像正常人那样生活。但是你已经看到我们这里的电梯了。所以我在家的时候反而觉得很不方便。每次上厕所都要花去我不少精力。一旦精力耗尽,就只剩下痛苦了。我的脊髓出了问题。以前就有这个毛病,他们给我做了些治疗。现在他们告诉我说这个病能治,但是我有可能失去平衡感。我每天都在左右权衡。我躺下来就什么事也没有。他们说,有些人得了我这种病,躺下来或者坐着不动的时候就会很疼。他们得不停地走动。我难以想象那种情形。”
威利又开始疼了。但是他想他应该说明来意。约瑟夫用双手做了个手势,示意威利不用说了。威利就不说了。
约瑟夫说:“你觉得这儿怎么样?和非洲比。”
威利想了想,却没有说出来。他说:“我始终对非洲人怀有同情,但我是作为局外人去看他们。我从来没有真正了解过他们。我通常是透过殖民者的眼睛去看非洲人。我和他们一起生活。但是这种生活突然间就终结了,非洲将我们团团包围,我们不得不逃离。”
约瑟夫说:“我在英国的时候,为了拿学位,选了一门关于‘原始政府’的课程。那时大战刚结束。金斯莱·马丁和《新政治家》的时代,乔德、拉斯基等人的时代。当然,现在他们不会叫它‘原始政府’。我很喜欢这门课。卡巴卡人、木嘎巴人、奥穆卡玛人,各种各样的酋长和国王。我喜欢他们的仪式、宗教以及神圣的鼓。许多事情我都不了解。也不容易记住。和你一样,我对非洲的态度是殖民者的态度。但我们一开始都只能这样。正是殖民者打开了非洲的大门,告诉我们非洲的情况。我那时候以为非洲就是丛林、大地,谁都可以自由来去。我甚至很久以后才明白,在非洲,进入别人的领地要付出代价,和别的地方没有两样。他们说它原始,可我以为这正是非洲胜过我们的地方。他们了解自己。我们却做不到。许多人都喜欢对古代文化等等发表宏论,但是你去问问他们什么是古代文化,他们却根本答不上来。”
威利昏昏欲睡,他在想厨房里的那个女人。他原以为她是直接坐在水磨石地板上,但现在发现她是坐在一条大概四英寸高的窄窄的矮板凳上。她的衣服和身体垂到了板凳外面,几乎把它遮住了。她的头被规规矩矩地包裹起来,因为威利是生客。她正在一个蓝边搪瓷碗里揉捏着什么。但是,她的后背和姿势表明她正在倾听起居室里的对话。
约瑟夫说:“我们生活在世界上最悲惨的地方。比你在非洲看到的要悲惨二十倍。在非洲,殖民历史也许还历历在目。而在这里,你无法理解历史,而当你开始了解历史了,你又希望一无所知。”
威利努力抵抗着睡意,强忍着突然醒来所带来的痛苦,端详着那个女人的背影,心想:“这正是萨洛姬妮在柏林告诉过我的。我以前就听说过。我那时候以为她只是在激励我。我为此尊敬她,但我对她所说的那些可怕的事情却是半信半疑。事实肯定就是如此。这是一项崇高的事业。我有信念,但我绝对不能受这个人的煽动。”
有那么一两秒钟,他打瞌睡了。
约瑟夫肯定注意到了,因为威利清醒过来时,感觉仍然站在沙发旁的约瑟夫丧失了一点儿活力和刚开始时的风度,说话更费劲了。
约瑟夫说:“印度所有的土地都是神圣的。但我们此刻所处的这方土地尤为神圣。我们正站在最后一个伟大的印度王国的土地上,这是一方灾难深重的土地。四百年前,入侵者结伙而来,把它摧毁了。他们花了好几个星期,也许是好几个月,在这里烧杀抢掠。他们将这座都城夷为平地。它曾是一座富庶的城市,盛名在早先的欧洲旅行家中间流传。他们屠杀了僧侣、哲人、工匠、建筑师、学者。他们知道自己在做什么。他们砍下了那些人的头颅。只有乡村农奴幸免一死,被他们瓜分了。战败的后果是惨痛的。你想象不到胜利者占有了多少而落败者丧失了多少。希特勒会称之为一场灭绝之战,没有约束,没有底线,真是一场非同寻常的胜利。没有任何抵抗。乡村农奴得以自保。他们来自许多不同的低等种姓,而各个低等种姓之间的仇恨是最强烈的。有些人奔走于主子的鞍前马后,有些清理废墟,有些挖掘坟墓,有些则献上了自己的女人。他们都把自己视为奴隶。他们都食不果腹。规矩就是这样。大家都说,如果你把奴隶喂饱了,他就要咬你了。”
威利说:“我妹妹也是这么对我说的。”
约瑟夫问:“你妹妹是做什么的?”
威利吃了一惊。不过他几乎立刻就明白了为什么约瑟夫不可能装作了解很多事情。于是他说:“她在柏林做电视。”
“哦。而且他们被课以重重赋税。总共有四十种之多。经历了四百年这样的统治,这里的人民越来越相信这就是他们永恒的生存状态。他们是奴隶。他们毫无价值。我不想提任何人的名字。但这正是导致我们神圣的印度式贫穷的根本原因,这种贫穷可以说是印度独有的。还有别的。最后一个印度王国被毁灭三十年之后,征服者们修建了一座凯旋门。如今这座凯旋门成了印度的文化遗产。毁灭的都城被遗忘了。战败是这样可怕。你或许以为,印度独立的时候,所有那些被征服者的主子们以及他们的家人都会被吊死,他们的尸体会被扔在那里烂到只剩下骨头。或许会有某种救赎,会有变革。可是没有发生这样的事。只有一些头脑非常简单的人提出了革命的标准。”
公寓的门忽然开了。一个肤色黝黑的大高个——差不多和约瑟夫一样高——走了进来。他的身材像运动员:肩膀很宽,腰很紧实,臀部窄窄的。
约瑟夫在沙发上坐下。他说:“政府以为我是在为游击队摇旗呐喊。不错。我就是希望有一场革命将所有的一切统统扫除。每当想到这里,我的心就感到一阵轻松。”
厨房里传来做饭的声音和香味,那些他自以为已经放弃的古老禁忌令他十分不安。那女人的姿态微妙地改变了些。
约瑟夫说:“这是我女婿。他在一家医药公司做研发。”
那个肤色黝黑、拥有运动员身材的男人,此时第一次把脸完全转向威利。他的嘴奇怪地一咧,似乎很开心:显然他很高兴自己的专业这么快就让陌生人知道了。但是,他的眼睛,眼角红红的,却充满了与之矛盾的愤怒与憎恨。
他说:“但是,他们一知道你是碰不得的,就不会想要和你发生任何关系。”
他本可以使用更温和的措辞,法律词汇、宗教词汇、政府许可的词汇。但是,当约瑟夫得体地介绍他的时候,愤怒、耻辱和自尊使他的嘴角不由自主地咧出一个微笑,同时也使他使用了粗野、过时的措辞。与其说是自怜,不如说是对外面世界的某种威胁。
威利想:“无论这个人怎么说,他已经赢得了他自己的革命。我没想到他们还在打这场仗。但是他让整个事情变得很难办。他要完完全全掌握一切。我想我不可能和他相处得好。但愿他们中间不会有太多这样的人。”
这个肤色黝黑、有着运动员身材的人大摇大摆地——在威利看来是如此——走进起居室尽头的一扇门。约瑟夫显然受了影响。他似乎一时间失去了滔滔不绝的能力。里面传来了马桶冲水的声音。威利有点儿相信,在约瑟夫这个小家庭里,在这套混凝土结构的简陋公寓里——曝露在外的电缆,约瑟夫未曾露面的女儿——革命已经造成了某种未被承认的破坏。
约瑟夫说:“是的,我就是希望来一场革命将所有的一切统统扫除。”
他不再说话了,仿佛是在脚本里寻找自己的台词。他从沙发底下拿出那个锡痰盂。痰盂的把手是用一根锡条焊制的,弯出时髦的弧度——工匠的杰作。锡条的边缘向内折起并焊牢,不再锋利,略厚,稍稍有点儿不规则,被摸得闪闪发亮。他捧着这个痰盂,大拇指摩挲着把手的边缘,似乎仍然在脚本里寻找被他女婿闯进来打断的台词。
最后他说:“但同时我对我们留下的人类也不抱信心,因为奴隶制度已经持续了好几百年。你看看那个小姑娘,就像个小蟋蟀似的。她是我们的用人。”
威利看着那个瘦小伛偻的身影。她已经从厨房走出来,进了起居室,蹲下来,一寸寸挪着步子,手握一把灯芯草扎成的小扫帚,小心翼翼地动着。她身上的衣服是黑色和泥土色的,就像是迷彩服,掩盖了她的肤色和容貌,剥夺了她的个性。她简直就是几天前威利在机场看到的那个女清洁工的缩小版。
约瑟夫说:“她就来自一个我刚才说的那种村子,那里的人都打着赤脚跟着洋主子鞍前马后地跑,在主子跟前,谁都不许穿能遮住大腿的衣服。她是十五还是十六岁,没人知道。她自己也不知道。那个村子里都是像她这样的人,又矮又瘦。人都跟蟋蟀或者火柴棍儿似的。经受了几百年的营养不良,他们的头脑已经不剩什么了。你以为你可以同她一起干革命吗?坎达帕里就是这么想的,我祝他好运。但是我认为,你在经历了非洲和柏林的生活之后,希望看到的不会是这些。”
威利说:“我没抱什么希望。”
“这里的人们说起游击队,就是在说她这样的人。这可一点儿都不激动人心。这里没有疲劳奋战的切·格瓦拉和硬汉们。这个地区一半的公寓里都有这么一个可怜巴巴的乡下女人,大家会说:没什么,这女人会胖起来的。老主子走了。我们成了新主子。那些不知情的人会一边看着她一边议论印度种姓制度有多残酷。其实,我们面对的是历史的残酷。而最可怕的一点是无从报复。老主子压迫、羞辱、伤害了这些人几百年。没人敢碰他们。现在他们走了。去了城里,去了国外。留下这些可怜的人做他们的纪念碑。我刚才说,你想象不到胜利者占有了多少而落败者失去了多少,就是这个意思。所有这些都是隐蔽的。如果拿非洲同这里作比较,你一定会说非洲要光明磊落得多。”
食物的香味更浓了,使早先的禁忌充满了威利的内心,使他越来越强烈地感到在这套革命者的狭小公寓里毫无幸福可言,而那个女儿已经成了一种牺牲。他希望主人不会请他留下来。他起身告辞。
约瑟夫说:“你住在里维埃拉。你大概认为它算不上合格的宾馆。可是在这里的人看来,它已经是高级的国际宾馆了。而那些你感兴趣的人,没有一个会去那儿找你。那太惹人注目了。有一家印度式宾馆叫新阿纳德宾馆,也叫‘和平新居’,是模仿尼赫鲁的宅子造的。这一带尽是‘新’这个‘新’那个的。是一种时髦。这家宾馆完全是印度式的,用蹲式厕所和澡盆。你去那儿住上一个星期,你感兴趣的人就会知道你在那儿。”
威利乘轰隆作响的老电梯下了楼。天色已然变成金黄。夜幕即将落下。尘土飘浮在金色光线中。但是孩子们毫不在意,依然在院子里的土堆间打闹吵嚷,心满意足的女人们依然在呵斥。就在不久之前,这一切还显得那么粗野、拥挤、无可救药。而此刻,再次看到这些,它们似乎顺眼多了,这让他感到喜悦。
![嫁给男主的偏执叔叔[穿书]](https://jmvip5.com/images/9969/e3a7d9b27ff2b09127c80629562ebb80.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