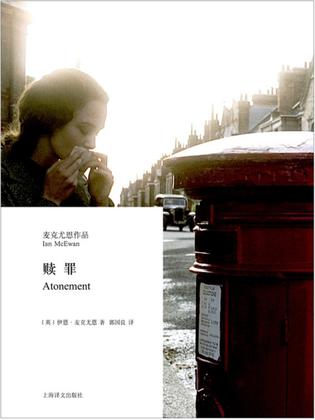师永刚提示您:看后求收藏(宜小说jmvip5.com),接着再看更方便。
<h3>传说的残骸</h3>
看到这座残迹的那一瞬间,单一海觉得自己终于看到了一种暗示,看到了那种在梦境中似乎才有的奇异,他的内心像被谁猛捣了一拳似的,发出叽叽吱吱的疼痛。那种透彻心肺的悸痛传达着一种针刺似的快感。他深呼一口气,任这快感在内心中四处窜游,心情豁地出现了一个窗口。一块明亮的窗口。
这块残迹在他眼中出现两年了。两年中,他每年都要利用夏天到这里看看。像看一个老朋友似的,他有种莫名的亲近。似乎这里才是他单一海最富有意义的地方。他很满意自己还有这种被冲撞的激动,这表明他还是多么富于激情。激情才是人年轻的激素!
他点燃一支烟,把迷彩帽从头上抹下,顺势把头上密集的汗液抹去,像抹去刚才短暂的惊讶,迅速恢复了以往的宁静。宁静地站在这块神秘的废墟上,对他几乎像是一种洗澡。一种只有用心灵才可以感受的被擦去污垢的清澈的安宁。
太阳这时又唰地下坠了一阵,刚才的艳丽尽消,圆圆的涨着红脸挂在焉支山梢口的风中,一浮一浮的。在西部呆久了,单一海有一种错觉,似乎太阳是唰唰地升起来,又唰唰地落下去。但这时似乎才中午两点整,太阳应该在自己笔直站立的头顶,可却偏斜着。一切的征兆,包括山呀什么的明确的物体都倾斜着。向西倾斜着。整个西部的地势,都像一条巨大的正在下滑的凝滞着的河流。这种倾斜在这儿明确到了让人悲哀的地步。可单一海似乎天生喜欢这种西倾的姿势。在他刚刚踏入这种倾斜的感觉中时,连精神上也立即趋于一致了。他在给女朋友邹辛的信中说“这是战士的姿势,我喜欢冲击的感觉,冲击令人神圣,西部就让我神圣,我指的是这儿似乎天生让我觉得西部从古至今,似乎只有战士、古战场、边塞等等才配拥有……”很是自我陶醉了许久。这种胜利像是一种精神上的美食一样,不可以吃但却扎扎实实地融进了单一海的血液。
单一海把脚蹬在一段山口上,回避着从稍西方向上直射过来的阳光。残迹像覆上了一层静悄悄的柔光,伴着寂静,几乎就是一幅被几百年前画好之后搁在这儿的一幅大尺寸油画。那种远远近近逼来的宁静的锋芒,有声有色地刺激着单一海,他有些不知所措地打量着对面这座过于突兀的残迹。不,准确地说,是一座残碎的城堡。这城堡,再准确地说,只是一片极像城堡的影子。它夹在焉支山脉接近主峰的地方,像一把兀现的利刃,刺击着这儿的宁静。单一海还是头一次见到这样一座废弃的城堡,居然建在海拔四千多米的高山上。这种高度和那城堡隐隐显出的肃杀,让他隐约有些伤感。他一见到这城堡,就隐约觉出这是一座兵营,是一座古代的战士们据守的兵城。这种发现激醒了他心中的血,他下意识地觉出一种亲切,一种隐蔽着的但让他特别激动的欲望哗哗呼呼地击拍着他的神经。好几百年前,几千年前,这座古城的主人是谁?那些将军,那些士兵,他们是谁?这些念头涌出来时,他竟有种无由的怅然。
去年深秋,连长单一海带侦察排班长冯冉勘察地形。地形勘察完了,他们发现了一只可怜的岩羊。岩羊真傻,见到人也不躲,还呆呆地望着这两个人类,单一海被这种冷漠激怒了,他想自个好赖还是个战士呀!真是和平了,和平到了连羊也不怕战士了,他对冯冉努努嘴,冯把装好子弹的“八一”式冲锋枪递过去。单一海接过枪,枪声真亮,岩羊在第一声枪响时,仍怅然地寻找枪响的由来。这呆傻再次激怒了单一海,他又一枪出去,鲜血从岩羊的肥臀上嘟嘟泻出。可怜的岩羊这才学会了逃跑。受伤的岩羊带他们翻过一道高坡之后,留下一些如梅花的血迹,闪进一片树林不见了,留下两个猎人在4265米的海拔上大口地寻找氧气。他们未打到猎物,却闯进了这片遗址。他们是上周进驻山上的,他的连队奉命随全团来到焉支山进行每年例行的野营驻训。夜晚露营后,他查对地图居然发现自己仅距遗址五公里,他悄悄地告诉了冯冉之后,便把这秘密压缩进了内心,他不允许战士们出入这里。他忽然有种强烈的占有欲。他觉得,这块遗迹似乎天生属于自己,他自私的把这块遗迹当做了自己的一块领地,一片精神上的军事禁区,他想在精神上保留一块战场,哪怕是废弃的沙场,也是一种胜利。
遗迹真像是一个人的脚印,可是这脚印真是太大了。
他凝视着低处的残迹,那是个奇怪的圆形的城堡。他的形状多么像是一个圆圆的大型的鸡蛋,蛋壳用黄土垒造而成,蛋壳内的城墙显示着当年房屋的规模。那是一种异族的形状和文化垒筑的东西,似乎与古罗马的建筑相似。但令他觉出兴趣的是那土城的造势。站在一个战士的立场,他很佩服那个当年垒城的人,城内弯弯曲曲的街巷如同一座小小的城市。那巷道却无时无刻不在地体现着军事用途。城有四重,四重的城墙垛上配置着的武器,火力密集,科学地体现着当年守城军士的智慧。这城在古代的战争中肯定从来未被击破过,只是未被战争破坏过的城墙却被时间无声的损坏了。一想到时间,单一海不由得想起土城墙那被风消蚀得只剩下土粉断垣的样子。有时候,他真想告诉那些整天喋喋不休的寻找时间的家伙们,你不是要寻找时间么?呶,你不用找了,这就是时间,只有这些残缺的被时间打败的遗迹,才配代表时间。单一海莫名的涌现出一种孤独,一种内心深处极端的悲凉。他忽然强烈的觉出,战士和战士,其实是一样的,其实是没有历史的,也没有时间。可是,对面的黄土内,那些人是谁呢?他们从哪里来,后来又去了哪里?
他并不比这座沉默的城知道得更多,他唯一可做的是他终于把这座城浓缩在了一张纸上,他有了这座残迹的草图就像有了什么证据。他找了许多人去问,去查了县志,但却仍是糊涂,可越是糊涂。他越想弄清这座城的由来。后来,他见了在凉州一家古籍研究所的一个古怪的老人,老人姓子,这个姓太古怪了,与他研究的学问一样怪。他在寻找一支失踪的军队,一支由古罗马战俘组成的军队。那个姓子的老者默不吭声地看了那张草图许久,才拍手大叫:“真是奇迹,它们真的在这儿,真的在这儿……与我想象的太一致了。”老人喃喃着,把急着要返回山上的单一海送出家门,郑重地握着他的手:“也许你发现了一支军队,也许只是一座旧城的残骸,可我没有证据,比如文字,比如他们残缺的脚印,比如残矢、脸孔……我需要你画出这座城详尽的地址和方位,还有一些实物。也许我们将共同发现一个二千年前的秘密。这也许是个可怕的发现。”
单一海驱车向山上野营驻地急驰时,内心像被攫住一样。他太压抑了,他觉得自己几乎被子老讲的那些话给压得喘不过气来,就把司机换了过来。在山坡上急速行进的吉普车,像一只小小的虫子,一会儿就蜿蜒到了驻地。
尽管老人的话只是一种猜想,可他真下意识的预感到自己正在接近一个秘密,一个只有在战士间才有的秘密。自从有了这个猜想,那种急切进入这块遗址的想法一下子变得有些沉重了,直到今天早上,他从梦中醒来,看到湛蓝的天空时,这种念头方又呼地燃烧起来,让他浑身不自在,他压制着自己没有半点流露。上午是政治学习,他向指导员交待了几句,就一个人出来了。那一段路他走的急如星火,全身出了许多的汗珠子。现在凉风刚过,全身舒服得骨头节吱吱响。他稍微整理一下自己的情绪,大步走向城堡的大门。那门只是两座土墙之间的一个缺口,他下意识地认为这就是大门。因为他注意到只有这儿才寸草未生。他下意识地挺胸收腹,感觉是在检阅。突然他又把腰下意识地挺直,仿佛城门边还立着个哨兵,也许就是那传说中的古罗马人,穿着汉族的衣服。并且是被汉族俘获的古罗马人。他们怎么来的,这么远,又是怎样在这里当起了战士。单一海的心中涌满了这些奇怪的问题。但他未作停留,任这些念头在脑子里晃悠。一瞬间,他甚至后悔,未曾向子老问及这些问题。未问别人,便等于给自己背上了一个疑问。有个疑问,总让人心里沉甸甸的,像挑着一担水,却不知这水是那口井里的。他习惯边走边想,一走路他脑子就特别活跃,特别适于思考。走路和思考,对他是一种巨大的享受,可这种享受在他还未进入大门时戛然而止。
他看见了一双清晰的鞋印。那两行鞋印从大门口大摇大摆而入,又悠然而去。已被风吹软的浮土才是最好的见证者哪!
可这人是谁?单一海有些突然的惊愕。
<h3>那个女人藏在他的背影中</h3>
那行脚印行走的方向有些不守规则,蜿蜿蜒蜒地像是叹息。从那行淡淡的脚印上,单一海仿佛看到了那个人偶尔驻足和呆呆仰望的神情。一个人的脚印就是一个人的表情哪!单一海在军校攻读时,读过一本关于脚迹方面的书。从那以后,他下意识地注意过许多人的脚印,从那些奇形怪状的印迹上,他读懂了许多自己未曾发现的东西,那些东西其实才是人最基本的表情。他下意识地保持着自己这一奇特的习惯。保持一种怪异甚至是独特的窥视方式,就像持有一种独特的认人方法和标准。
他跟定那行脚印,从土墙进入这座残缺的古城堡。堡垒内的阳光似乎被那些土吸走了一般,倏然暗淡了下来。单一海镇定一下,看准方位,摸出纸笔。他决定先不去理会那行脚印。这也许只是一个牧羊人的足迹吧!一个孤独的牧羊人!但他忽视了这个牧羊人的羊群。他有种深深的冲动,描摹出这座城的每一点细微末节,并且尽可能找出一点实物,如果可能,他真想让自己的连队,把这座城挖地三尺。他想,肯定会有一些残矢或者那些战士的骨殖开口说话的。为子老提供一个可供判断和佐证的东西,也为自己。
他把那张绘图纸在图板上固定好。淡淡的微风哗哗地掀动着它,发出啪啪的带有金属质的回响。单一海很喜欢这种纸。硬韧光滑。一看就有种想在上面挥毫的冲动。他还有个私人的小毛病,凡属一些重大的材料或者标图,他都爱找来这种纸,用以实施个人的想法。他觉得,高质量的东西必须要有高质量的纸张才相配。一看到那种把高质量的东西用软不拉叽的白粉纸表现的行为,他就觉得有些说不出的不舒服。今天,他特意把那几张好纸拿来。他想,我肯定可以把这座城绘好,并且一次成形,永不改动。
单一海有这种能力,他比任何人都信服自己的本领。他在陆军大学指挥专业学了三年,此后又在司令部绘了三年地图,垒了三年沙盘。在十年间几乎绘遍了自己驻防地域的所有地图,并且差距仅万分之三。要知道,这是手绘呀!他的参谋专业几乎成了这个集团军参谋专业的标高。他可以用一把尺子,一只铅笔,当然还有一张上好质地的高标绘图纸,靠目测就可以准确地复述你随手指定的某类地形地物。但他天生不爱在平静的司令部机关闲呆,他用了一个不过分漂亮的借口,终于到了这个乙种师的168团当了二连连长。这个连长太悲哀了,悲哀到了一种连他的专长也一无用处的地步。战士们并不需要他做任何类似的表演。
他已有一年时间,收藏起了这种特殊的专长。
他在等待那种深深的从精神上覆盖一座山的快感。他拿出指北针,在图板上放好,对准大门。他迅速发现了这座城的怪异,城偏着西。也就是它的大门开得毫无规则,或者说,这座门并不是按传统的中国建城规则,天圆地方,四方四正,正东正西,不得有丝毫混差。而这城的大门,却是在偏西上。他有些稍微的惊奇,迅速走到门前150米远处的一座高岗上俯视,这座城竟只有这样一个偏西的大门,他忽然觉出一种深深的寒意和悲哀。这些守城的战士,只给自己留了一个门,还是战斗的门!也就是说,这座城和这些士兵永无退路。从一开始,他们就给自己定了一个标准,一个战士的标准:只有胜利,否则死亡。明白了这层含意,单一海脊骨间涌起阵阵寒意,他闭眼定神,似乎要从中挣扎出什么似的。他提笔疾画。仅片刻,那座城的轮廓和概貌便挪到了纸上,但中间却是一片空白,他忽然想把这四重城内的全貌用线条和代码全部画出来,他觉得那些传说中的战士,也许正在城内隐藏着。
他重又进入土城,这次他决定,凭直觉前行。在山上他已看出,这座城近似迷宫,四重内又是四重,似乎永无尽头,又似乎一步到头。所以,他那次与冯冉在城边上驻足良久,还是未敢轻易进入。他忽然想起那行脚印,是谁,竟敢轻易入内?
城内的土屋残壁已被风化,有的只剩高高的一堵大墙,中间却洞开着,风从中间跃过时,呜呜的如同吹胡茄。城内残垣密集,回音效果奇好,到处一片肃杀的低鸣,仿佛是一些绝音,夹着风尘,一点点地来回走动。单一海每走十多米,都用残石碎土,用自己的理解,在地上摆成一个小小的沙盘或模型,直到自己满意了,再在图上留下一片小点。他准备把全城用模型局部凸现完毕后,再进行详画。还有一个作用,他把这当成了路标。
转过一条貌似街道的路后,他又触到了那行脚印。那行脚印时隐时现,令单一海有种无由的亲切。这个牧人居然与自己的直觉有些相似。至少与自己这半个小时的直觉是吻合的。他忽然对那脚印产生了兴趣,他觉得这个人只要不离开他的直觉,他肯定可以凭直觉找到他。他顺着残道前行,看到一堵残垣挡住了去路。面前一下出现了三种选择,左右各有一条小路,但那行脚印却直接从残垣后面绕了过去,他停顿了一下,略作思索,选择了向左。他对那行脚印本能地产生了一种拒绝,他本能的认为那行脚印是正确的,可却又希望它不正确,也许只有这样才可以证明自己的高人一筹。单一海想着,已悟到再向左走,只是一条死路。他本能地回转身,绕过残垣,向前直走。前面是一段石板,上面的脚印失去了。单一海觉出片刻的轻松,拿出指北针,判定自己还是在正北方向。他在每个重要的地方都堆了个小小的模型。现在,这半个城的许多局部都在他的心里自动组合,揉捏成了一个整体。迎面是一排房屋,还有一口井,似乎每间屋里还有炊烟的迹痕。这应该是住人的房子。可这房子这么小,像一个个住家的单元,更像是战士们的家。家,一想到这个字眼,他的心里不由一动。内心温暖了一下,又被片刻的惊讶给淹没了。此城的设计者肯定是个大胆无知……又谋略超群的家伙。他太狂妄了,狂妄到忘了给自己留一座逃跑的门的地步,无知到了把家属妻儿摆放在城门边缘。这正是兵家所忌呀!可这个家伙全然不顾什么兵家所忌。他按自己的思维和权力,为自己和自己的属下造了一座坟墓式的老城。而几千年来,居然从未被击破!忽然,单一海有些心悸般的敬佩起那个无名的家伙了,此人真狂啊!他感叹,从一开始,他就为自己和属下们断了逃跑的路径,他不允许自己的兵们,留出心思来寻找生还的路径,他把你的亲人放在你的身边,让他们温情的目光盯住你。这样的驭兵之道比他的“破釜沉舟”还“破釜沉舟”,这是一种大绝望,也是一种大勇气,更是一种大战士风度。
他不由得有些坏坏地笑了。大步越过半堵破墙,那行脚印又出现在了他的路上,真邪了,他暗自惭愧。这个人仿佛路标,仿佛城内的主人,到处转悠,从脚印上看,似乎全无顾虑,全无徘徊,甚至没有哪怕一丁点的犹豫。似乎边走边欣赏,只是随意走去,便走通了一座迷宫式的兵城。单一海有些莫名的愤怒。他觉得内心中仿佛有什么被占领了似的,老觉得有双脚在踩击着他,让他疼。他恼怒地蹲下来,认真地盯着那双脚印,那脚印不深,浅浅的,从尺寸上他判断有37码,也就是说,此人身高1.62米左右,又是一个小个子。他继续读着那鞋印,这竟是双部队配发的87式迷彩高腰胶鞋的印迹。这种鞋子刚装备部队不久,穿着舒适,看着帅气,官兵没有谁舍得拿这种鞋子给老百姓换鸡蛋吃。是连队里谁吧?比如冯冉,也不可能,临出门时,他还看到他在连队。从这鞋印上看,肯定是刚刚踩上的,而且,他凭感觉,此人肯定在前方不远处行走,还没走出去。这个发现让他内心一动,也许是一个对这座城堡有兴趣的人,可他会是谁?他起身又跟着脚印走了几步,判断出此人体重最多50多公斤,也就是说,此人体重偏瘦,从行走步幅的方式上看,似乎……似乎是个女人!穿一双迷彩胶鞋的女人!他被这个发现吓了一跳,抑或有种惊讶,更多的是激起了自己的好奇。他迅速起身,跟着那脚印前行,又走了几十米。虚浮的土已被茂密的草木遮住。草棵子很深,偶尔哗地飞起一只野鸽子,倏地又消失了。太阳此时被城墙挡住了,单一海无法判断时间,他的头脑中有些乱哄哄的,神秘的女人、遥远的来历不明的战俘、城中曲折的小径乱七八糟地涌在他心里。心神一乱,他的直觉就产生了问题,他越过一堵墙,过了几分钟,他又回到了那堵墙边儿上,他知道自己迷路了。他有些愤怒地捶了一下自己的脑袋,蹲在地上出神。半晌,待心神稍静后,他拿出指北针,重又确定方向,决定原路返回。
原路真好找,他很满意自己那些小小的模型,他一路上只找这些自己摆放的路标,它们此时静静的摆放在那里,每过一个小模型,他都有种行走在微缩了的这座残迹的快感。但渐渐地,他看到,在有浮土的地方,又多了一行鞋印,也就是说,那个人也返回了,或者是说他(她)也迷路了。这样一想,他竟有种无由的欣悦,毕竟她的直觉也与我一样,并不超群。但很快,单一海就发现异样了,他看到那脚印在他垒的每个模型前都略有停顿,并显得有些杂乱。很显然,这个人认真地审视过它们,让单一海略为惊讶和不满的是,他垒的几处模型已被人悄悄挪动和删改了。有一处表现古井和炮台、堡垒的三角模型被改得几可乱真,很细腻地呈现着实物的韵味。他稍微欣赏了片刻,看出那人没受过任何垒积训练,但却对环境有种天然的逼真的摹拟感。
他不再孤独了。单一海叹息了一下,缓步向前走。那条土街的两边长满了高高的密草,有的竟如小树林,十分粗壮。他不再关切这些,顺手点燃一支烟,深深吸了一口,抬眼瞥见街前30多米处奔出一只肥硕的大兔子来。它似乎受到什么惊扰,哗哗地撞断许多草枝,向他跑来。好大一只兔子!他大呼一声,迅急朝兔子追了过去,那兔子太笨,眼见单一海过来,却来不及转身,竟在原地打了个滚。单一海心中暗叫着乖乖,就要伸手去捉。兔子从他手中挣脱,又向前跑去。单一海爬起又追,就在距那兔子三米远左右,单一海只觉耳边裂帛似地一声枪响,眼前红光一闪,那兔子翻身倒地,又挣起来,撞断几棵篙草,一头栽在草丛上,身上涌着汩汩的血。
单一海那一刻觉得有些异样的惊骇和恐惧,一下子呆住了。内心中瞬间空白。那是一声枪鸣,从刚才的声音上,他判断是一支猎枪发射的子弹,子弹是狩猎用的散弹,内装六颗铁丸,射击半径正好两米左右,也就是说,他再往前跑半步或者一米,必有一颗铁丸嵌进自己的身体。要命的是,枪只打中了那只兔子,这家伙枪法好到了要用他这个活物作陪衬的地步!那一瞬间,单一海又气愤又恐慌,他知道自己在这个地方行走时,那支枪和两只眼睛已跟踪了他许久,而自己居然一无所知。他不由一阵后怕,要是那颗子弹将自己谋杀掉,那自己临死也无法窥见凶手一面了。他对自己产生了深深的失望。他只有呆呆地站着,等那个狩猎者自己出来,此时,再作任何表示躲避,比如在地上迅速滚进之类的动作,都将只会成为一场可笑的表演,甚至增加对方自我欣赏的快感。
他定了定神,大步走去,把那只兔子拎起来,看到三颗铁丸全部散布在那兔子的身上,枪法真准呵!这个混蛋。嘴上却大声喊:谢谢你把这么肥的兔子送给我。说完,拎起兔子就走。
话音未落,从刚才射击过的草棵子后面摇晃出一个人来:“哎,你这人怎么这么不讲理,那是我的猎物呀。”
单一海被那声好听的女音撞击着,嘿,是个女的,果真是个女的!听声音,还是个姑娘。他咬着牙:“我也是你的猎物,为什么刚才不给我一枪,你的胆子也太大了吧!?”
“想当兔子还不容易,能撞到我枪口上的人,你是第一个。”话音未落,单一海便觉得头顶上“眶”又是一枪,霰弹的啾啾声撕裂着寂静的空气。单一海仍不回头,内心中却被这枪声惊得一忽悠一忽悠的,他感觉出那姑娘在距他十米左右,正仰角发射,枪声距他很远,这是个至少不那么特别让人烦的姑娘。可却是个让人害怕的女人。他想,如果她不是当地猎户的女儿,那么她就是随团卫生队来出诊的三名女军医中的一个。那三个姑娘迄今他只见过一个,丑丑的矮矮的,他感冒时去输液,那胖姑娘足足用了半小时才找到了他的血管。
但愿不是她们中的一个。
“哎,你怎么一点也不怕?小中尉。”单一海听出身后那个女人轻轻跺足。猜测她也许很好看,因为这一跺足明显的有些撒娇。同时,他也悲哀地觉出,这女人是个军人,因为她可以看懂他的军衔。还可以讲略带家乡味的普通话。本地女人又土又纯朴,不会像她这样讲话。
他觉得晦气十足,打定主意不回头,他觉得自己没有对付这类女人的经验。
“我料定你不会向一个陌生男人开枪,何况,你知道自己的枪口应该对准谁,而不是我。”单一海硬硬地说,把兔子随手抛在地上,“野兔在打死一个小时后剥皮,烧烤,是一道最佳的野味……哎,可惜了,死在一个不懂如何享受猎物的人手里,我为它不幸。”
单一海耸耸肩,扬长而去。
“站住,胆小鬼,你以为你这样说几句俏皮话就是幽默,就是潇洒啦,我最讨厌你这类男人了,又虚又假,明明恐惧,还强作潇洒,明明害怕,还强作英勇状。你以为你走了,我就会自责啦,告诉你,刚才我还有道歉的不安,现在没有啦,你真没劲,没劲到了不敢回头看看向你开枪的人!”身后女人的口气似乎充满了极度的愤怒和……失落。她以为这个被惊吓的男人,肯定会转过一张极为惊恐的脸面对她,但今天这个家伙居然高傲到了不愿回头看她一眼的地步。这已经不是对她的无礼,简直是轻蔑了。
单一海并没有驻足,他快意地吹起了口哨:啊,朋友,再见。哨声响亮,甚至刺耳。他向山下走去,刚走出几米,单一海听到身后头顶上“哐”地又是一枪。一只鸽子扑地落在他身边,他下意识地一蹲,双手捂住了脑袋。身后刺耳的尖笑声响作一团。他不由沮丧地闭上了眼。后悔自己居然没有能坚持住。他朝地上砸了一拳,恶狠狠地为自己悲哀。我还是怕了,唉,我以为我是不怕的,其实潜意识里还是在怕。唉,谁也不可能躲过去呵!这些悬垂着的怕。可我怕什么呢?怕一个狩猎的女人指向不明的枪口?人呵!其实最担心的还是背后的枪口。单一海惭愧自己也有这样的恐惧。只是……那女人仿佛未曾向他开过枪似的,接着他刚才吹的“呵,朋友,再见,”摇曳而去。单一海缓缓抬起头,正好看见一个极婀娜的背影从眼前晃去。他忽然觉出这背影真美,女人着一身军装,尤其是一件只有军队上才有的迷彩服,会有一种新的韵味。他轻轻的咀嚼着那女人的后背,忽然听出她哼的那曲子极准确,第一句正好接上他刚才被一惊而未哼出的第二段的第三句话。那女人走过他身前数米,亭亭转身,单一海发现这女人美得足以让人一下子忘记了仇恨。
他蹲在那儿,感觉像一朵过秋的向日葵,枯萎了。
<h3>直觉的重复</h3>
“我还以为你不怕呢?没想到,你真的怕。”那女人居高临下地看定单一海,轻声低语,但没有丝毫的嘲弄。仿佛是在与他探讨什么事儿,倒忘了自己的恶作剧。
单一海有种被轻视的痛苦。他认真的看这个女人,哦,她真好看,尤其是那双眼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