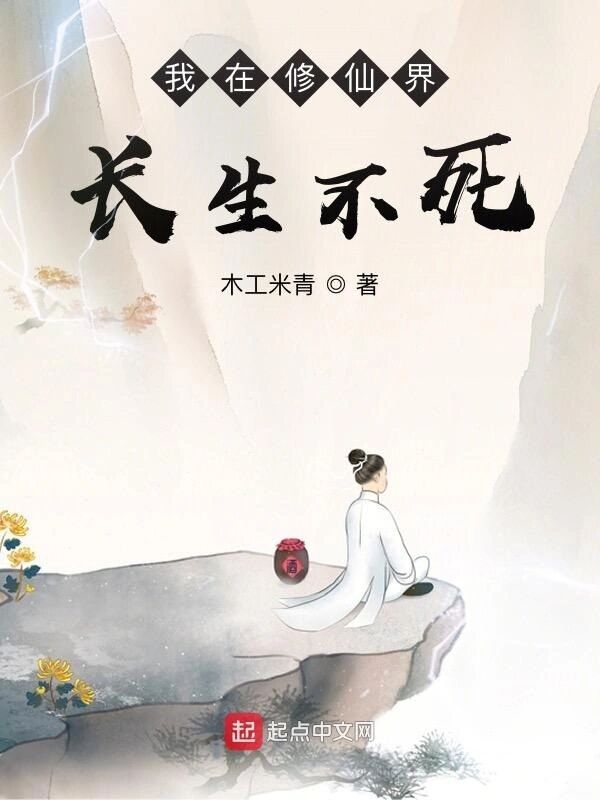奥里亚娜·法拉奇提示您:看后求收藏(宜小说jmvip5.com),接着再看更方便。
马卡里奥斯大主教,户籍登记名米哈伊尔·赫里斯托祖卢·牟斯寇斯,于1913年8月13日出生在塞浦路斯帕福附近的阿诺帕那基阿。在雅典就读并成为神甫。之后,到美国继续他的学业。回国后,个性极强的他成为大约占人口80%的塞浦路斯希腊族人的宗教和世俗领袖。1950年,被选为塞浦路斯东正教的大主教,称马卡里奥斯三世。他公开支持那个时候仍属英国殖民地的该岛与希腊合并,但是后来趋向独立。1956年,遭英国人逮捕。翌年,由于希腊发生全国性的动乱而被释放。1960年,塞浦路斯取得独立,宣布共和。他被选为总统,至1977年8月3日在尼科西亚去世前一直就任此职。
当我们谈到某个问题时,我对马卡里奥斯说:“您使我想起了简·奥斯汀的一个忠告。”“简·奥斯汀的什么忠告?”马卡里奥斯笑着问道。“一个聪明的女人永远也不应该让人知道她有多么聪明。”“但我不是一个女人。”马卡里奥斯笑道。“是的,但您是个聪明的人。您是如此聪明,以致正在千方百计地不让我察觉到您的这种聪明。”我最后这样说道。于是,他的目光变得严峻起来。他身上似乎有某个东西弓了起来,如同一只弓着腰准备投入战斗的猫。我也弓着身子,静待着他用爪子扑过来。我准备迎战。但是他没有用爪子来抓我。他像刚才瞬间发怒时那样,瞬间又恢复了镇静,继续说道:“就像我向您解释的那样,我是个幸运的人。我知道在我升入天堂之后,报纸将会写些什么。今年7月,我读到几篇有关我的讣闻,它们是如此可爱。您记得吗?他们以为我已经离开尘世。我的大使们收到的电报也是可爱的。最可爱的一份电报来自塞浦路斯的最后一任总督和夙敌凯雷唐勋爵。后来我在伦敦会晤了凯雷唐勋爵。我们谈到了我们过去争吵不休的关于保留在塞浦路斯的英国基地的期限问题。我对他说:‘那些基地仅仅有利于一件事:它使我在政变后安然无恙,并帮助我离开了这个岛屿。’”这就是马卡里奥斯吸引我,并被列入我所喜欢的人数不多的当权者人物之中的原因之一。
本来,我并不喜欢他。有一次,我还想方设法要向他表明这点,而结果却接受了他的祝福。当时,正值胡安·卡洛斯和索菲娅的婚礼,他在雅典,下榻大不列颠饭店,我也住在那里。一天晚上,他来到饭店门厅。只见他衣着华丽,宛若一尊圣像,身上的金银珠宝闪闪发光,手握总督的权杖。他一出现,门厅便成了一座小教堂。有人弯下身子,直到把鼻子碰到肚脐附近,有人跪在地上,有人想吻他的手,至少想吻他的衣服。唯有我昂着头,而且坐在一张高高的沙发上,因此十分引人注目。沙发处于电梯和大门之间,他一眼就发现了我。他盯着我,流露出愤怒、惊讶和痛苦的神情:“这是什么人?怎么敢?”他庄重地向前走,一直来到我的面前,停住了脚步,冷冷地瞥了我一眼,为我祝福。没有必要去说我当时并不愿意接受他的祝福,现在回想起来仍感到别扭。如按世俗人的良心来衡量,马卡里奥斯至少是个令人讨厌的人,因为他是世俗权和神权的最牢固的结合的反映。他像一个坐在奎里纳莱宫而不是坐在梵蒂冈的教皇。他是东正教教会的领袖,同时又是塞浦路斯的总统。你永远也不知道向他提问时应该把他作为一个宗教领导人呢,还是把他作为一个政治领导人,你永远也不知道是称呼他为宗座呢还是总统,是称呼他为大主教呢还是马卡里奥斯先生。他是由民主选举产生的。尽管如此,也无法使你忘记一个痛苦的现实:他是因为同天堂有关系而获得这些选票的。对于塞浦路斯的农民来说,投票选举马卡里奥斯这件事与行圣礼相似。据说,甚至连共产党人在投票选举他时也都要画十字。然而,然而……他是一个即使不是真正值得拜倒在他脚下,也是值得令人肃立起敬的少数几个国家元首之一,因为他是少数几个有头脑的国家元首之一。除了有头脑,还有勇气;除了有勇气,还有幽默感、独立见解和尊严。这种尊严与一位近似国王的尊严相似,只有上帝才知道它是怎样产生的。他的父亲是个目不识丁的牧人,他本人直到12岁时还在放牧羊群。
许多人都不喜欢他。譬如,有人指责他沉溺于女色,或者曾一度过于沉溺于女色,指责他不论哪一方面都不是个禁欲主义者。我相信这一点。但我不相信对他的另一项指责,说他靠谎言、阴谋和冒险掌权,除非把他的擅长算计说成谎言,把他的灵活说成阴谋,把他的想象力说成冒险。他这个人物不能用西方惯用的尺度来衡量,他不属于西方。他属于既非西方,也非东方的某个方面。他深深扎根于一种既风雅又古老的文化中:落难中求生存的大师。他通过以足绊人、以手拧人、狡猾的计谋、清晰的头脑和老于世故屡次化险为夷,求得生存。有人曾四次图谋暗害他,他四次幸免于难。有人曾两次将他发配到流放地,他两次安然返回。唯有一次,也就是当雅典法西斯军政府靠政变推翻了他的政府,并图谋杀害他时,他似乎不可能东山再起了。但即使在那种情况下,他也幸运地逃脱。他先在英国基地避难,后由那里取道前往伦敦。结果,付出血泪代价的是塞浦路斯人民。事实上,校官们的政变导致了土耳其的入侵、战争、屠杀和岛屿的事实上的分裂。这是一场连大国的协议和联合国的决议也难以平息的悲剧。从那时起,塞浦路斯成了地中海中一根燃烧着的导火线。
采访马卡里奥斯是几个月后在纽约进行的。那几天,联合国正在讨论土耳其从其在塞浦路斯岛的占领区撤退的问题,而这种撤退的可能性是不存在的。会议处于白热化状态。为了听取会议的讨论情况和监视那个他想见一见的基辛格的举止行动,马卡里奥斯中断了伦敦的流亡生活,在普拉察饭店订了一套房间。他在无数卫队士兵的保护下在那里筹划回国之计。我在那里见到了他,先后两次同他共进行了约六小时的谈话。他没有像以往那样穿戴着挂满金银珠宝的华丽服饰,他接见我时穿着一件十分端庄的蓝色长袍。当时,他61岁,但外表显得比年龄更老,似乎他所经历的悲剧使他一下子变老了。我们几乎很快就打破了寂静,也就是当我问他能否抽支烟时寂静就打破了。我忘了别人对我的叮嘱:会见他时不要抽烟,因为宗座忍受不了烟草的气味。但是这一次他却叹了一口气说:“我能抽吗?我太想抽烟了。”说完,他给我看了看被尼古丁染黄的手指。这与其说是打破寂静,还不如说是一种默契:荒唐可笑而又意想不到的默契。数年前,我还觉得这个人是个可恶的敌人,而现在却在我的面前成了个可尊敬的人,一个天禀聪颖而光彩夺目的人。我对我们所谈的一切都感到兴趣十足,甚至感到欣喜万状。交谈过程中,他时而穿插进一些奇闻轶事。他才思敏捷,只要一提起某个名字,如铁托,或毛泽东,或纳赛尔,或周恩来,就足以使他从中敷演出一段历史,描绘出一幅令人入迷的画像。不用说,我是怀着感激的心情倾听着他诉说他对独立和自由的酷爱的。关于马卡里奥斯,人们可以写一部绝妙的书!当然,在这种情况下,我不愿意取基辛格的角色来写这部书,因为他是马卡里奥斯深恶痛绝的人。当录音机的话筒关上的时候,他直截了当、毫不含糊地告诉我说,美国国务卿和中央情报局对塞浦路斯的政变事前早有所闻。“是基辛格开了绿灯!”当他说这句话的时候,他的声音失去了惯常的温和语调。
我们作为朋友相互道别。在门口,他低声对我说:“简·奥斯汀的那个忠告……对您也适用。可惜您是个女人。”我回答他说:“可惜您是个神甫。”后来,我们约定在塞浦路斯再见。我当时就预见到他将会一帆风顺地回到那里。八个月后,我同亚历山大·帕纳古里斯一起在那里果然又见到了他:在一次礼节性拜访中见到了他。(1968年,那些校官在全岛搜捕帕纳古里斯。由于马卡里奥斯委托其属下的内政部长盖奥尔加吉斯给他发放了一张假护照,帕纳古里斯才免遭逮捕。)他在政府大厦中一间朴实无华的办公室里接见了我们。他请我们喝咖啡。他摆动着食指抗议道:“您在那次采访中让我说了些什么啊!我当时实在不谨慎。”与此同时,他的眼睛里流露出笑容。但是他的面容已变得更加疲惫不堪,他的背驼得更厉害了。他成了某个政权的具体体现,这个政权就像流着血的伤口那样在受苦受难,但它却是唯一能为世界接受的政权。
奥里亚娜·法拉奇(以下简称“法”):宗座,我提一个鲁莽的问题:您是否还要回塞浦路斯去?
马卡里奥斯大主教(以下简称“马”):我当然要回去,这是肯定无疑的!我将于11月回去,最晚也不晚于12月。行期将完全由我自己决定。我至今尚未回去,只是因为我等待着希腊政府撤换那些在反对我的军事政变中负有责任的军官,也因为我想留在这里亲自听取联合国关于塞浦路斯问题的辩论。我并没有提出过辞职,我不明白,为什么要对我回国一事提出疑问。我没有任何理由不回国,除了那些担心自己将受到审判和惩罚的人之外,也没有任何人反对我回国。我不打算去审判和惩罚那些人,那将有损于国家的团结。不言而喻,这并不意味着我企图歪曲历史。恰恰相反,我愿意全世界都清清楚楚地了解所发生的事件。但是我愿意摒弃种种惩罚和报复的手段。我将宣布大赦,那些因为我要回国而吓得发抖的人可以安心。何况,他们是为数很少的几个人。与军事政变前相比,今天人民更加拥护和支持我。他们渴望能再见到我。99%的人是站在我一边的。
法:99%的居民包括土耳其族塞浦路斯人在内。宗座,我不相信他们会满腔热情地想重新见到您。
马:我同意您的说法,我也不认为大多数土耳其族人会拥护我。恰恰相反,我以为就是土耳其族副总统登克塔什<small>[1]</small>先生一想到我要回国也是不高兴的。但是我并不为此担心,将同登克塔什先生和土耳其族会谈的不是我本人,而是克莱里季斯
<small>[2]</small>。他是个杰出的谈判者,比我更了解登克塔什。噢!当然毋庸讳言,未经我的许可,克莱里季斯将不得作出任何决定。也毋庸讳言,当我谈到返回塞浦路斯时,我谈的是作为总统返回塞浦路斯。我是总统,我将作为总统回到那里。如不是作为总统回到那里,我决不接受。我是否还将在一段长时间内担任总统?这仅仅是我个人的事,也就是说我将在塞浦路斯作决定。我现在告诉您吧,我并不排除再过一段时期后放弃总统职务的可能性。我必须根据形势作出判断,譬如,一旦达成一个可恶的协议,那么我不应该再继续担任总统。但我再说一遍,这要等到以后再决定。
法:可恶的协议应怎样理解?
马:土耳其将坚持建立地理上的联邦,这我决不接受,因为它将导致这个岛屿被分割并出现双重的归并:塞浦路斯的一半交给希腊,另一半交给土耳其。这将意味着作为独立国家的塞浦路斯寿终正寝。是的,我准备讨论建立联邦的问题,但这个联邦应该是行政意义上的联邦,而不是地理意义上的联邦。出现一些土耳其族人执政的地区和一些希腊族人执政的地区是一回事,把我们分成两部分则是另一回事。把两三个土耳其族人居住的村庄合并在一起,然后交给一个土耳其族人的政府管辖是一回事,把20多万人从岛屿的一个地区移到另一个地区又是另一回事。土耳其族塞浦路斯人分布于全岛,怎么能对他们说,为了建立联邦,你们卷起铺盖,离开你们的家,离开你们的土地,迁居到另一个地方去呢?这至少是不近人情的。
法:宗座,这正是使您感到苦恼的事吗?难道是土耳其族塞浦路斯人的悲剧使您感到苦恼吗?我并不觉得直到昨天为止他们是分外受到尊重的人。他们被当做二等公民和……
马:这并非事实!这并非事实!尽管他们是少数民族,但他们有很多特权,他们的举止行动表现得像是大多数人的代表一样。虐待他们的不是我们,而是他们的土耳其族首领:这些人强迫他们生活在与世隔绝的村庄里,对他们进行讹诈,阻止他们在经济方面同我们合作,阻止他们进步。这些人不允许他们同我们进行贸易,同我们一起发展旅游事业。他们不是我们的牺牲品,而是那些人的牺牲品。谁也不能否认,在塞浦路斯存在着真正的民主,完善的民主。土耳其族人可以在他们的报纸上随心所欲地折磨和咒骂我,他们可以到大主教府邸按照他们的意愿见我并向我提出问题。糟糕的是他们由于受到自己首领的逼迫只能秘密来找我。塞浦路斯两个民族曾杂居在同一个村庄里,而未曾发生过什么问题。过去如此,就是在希腊与土耳其交战时期也是如此。您说的并非事实。
法:宗座,您剥夺了他们的许多宪法特权,这是真的吗?
马:我没有剥夺他们的任何特权,我只是悲叹那些特权使得国家机器不能正常运转而已。宪法规定,他们以30%的比例参加政府。但在很多情况下,担任这30%政府职务的土耳其族塞浦路斯人往往缺乏能力。譬如,有一个职位,本来可以由一个聪明的希腊族人占据,而结果却不得不交给一个目不识丁的土耳其族人,仅仅因为这个职务非得由土耳其族人担任不可。有一次,他们投票反对税收。我想方设法向他们解释公民不纳税,政府也就难以存在的道理。他们拒不接受。于是,我就强迫他们照样纳税。这是滥用权力吗?另有一次,当我准备去贝尔格莱德参加不结盟国家会议时,登克塔什先生想行使否决权,阻止我去。我回答他说:“尽管您行使您想行使的权力,我还是要去。”这是滥用权力吗?
法:宗座,不管您说的是否有理,今天的现实已经发生变化。土耳其族人占据着整个岛的40%……
马:我不能接受这一说法。因为我不能承认“既成事实”,我不能以我的签字使通过武力造成的形势合法化。所谓的现实主义者建议我同土耳其族人商谈建立地理联邦的事宜,认为我理应是个不太强硬的人。他们一再说,他们将能满足于30%,而不是继续占据整个岛的40%:可以是灵活的。我不要这样的灵活。
法:“灵活”这个字眼是亨利·基辛格所喜爱的。是他对您这样说的吗?
马:基辛格从来没有明确地对我说过他赞成建立地理联邦。他从来没有明确地对我说过他正在做什么。他总是对我说“为双方都能接受的解决办法”。他总是翻来覆去地说:“我们不打算谈我们为说服土耳其而正在做的事。”这样,我也就不能断言他正在酝酿一个为我所不能接受的协议。但是我可以告诉您说,我们在很多很多的事情上看法仍不一致。如果美国愿意的话,那么它在这件事上能够起到更有决定性的和更加明确的作用。不是它在向土耳其提供经济援助和武器吗?不是只有它才能够说服,甚至迫使土耳其变得更加理智吗?
法:宗座,您相信未经基辛格的默许,总之,未经美国人的默许,塞浦路斯可能发生这样或那样的事件吗?
马:噢!我相信,美国及其他国家事先就得到有关土耳其当时正在准备入侵塞浦路斯的消息。也许他们受了土耳其人的骗,也许他们中了圈套。当时土耳其人告诉他们说,这将是一次有限行动,一次旨在两日之内恢复宪法秩序的警察行动。也许他们很晚才了解到土耳其的真正计划是什么。但是,他们本来仍然可以制止事件的发生。他们可以拦住源源而来的土耳其部队。我就此事同基辛格进行了长时间的讨论。我向他表明了我的失望。我毫不掩饰地告诉他,我对他的国家所采取的态度是何等不满。
法:他怎么说?
马:他回答说他不同意我的看法,他回答说他在幕后奔忙,做了说服土耳其人的工作。就是在这次讨论中,他也不愿意明确地解释他究竟做了些什么。
法:宗座,许多人觉得基辛格和美国应负的责任远不是在土耳其入侵塞浦路斯的问题上,我们没有忘记入侵是在继雅典军政府发动了推翻您的军事政变之后发生的。还有……
马:当然,悲剧的第一章是由雅典军政府写下的。塞浦路斯首先是由于希腊的干涉而遭到破坏的。土耳其作为第二个祸害接踵而来。提起此事,我犹感遗憾,因为希腊现政府对待我很好,以诚挚和坦率对待我。我没有见过卡拉曼利斯,也没有见过阿韦罗夫<small>[3]</small>,但是我认识马夫罗斯<small>[4]</small>。我喜欢马夫罗斯。他是个精明能干的人,是个诚挚而坦率的人。对我来说,他这些优点足够了。但事实依然是,如果塞浦路斯当时没有失去自由,那么希腊也绝不会恢复自由。事实依然是,如果前任政府,即军政府没有给土耳其人留下口实的话,那么土耳其永远也不敢进行干涉。土耳其威胁要入侵我们由来已久,但是他们始终没有付诸行动,因为他们始终找不到进行这种入侵的口实……
法:是的。但是您不相信美国或者中央情报局同那次政变有某种关系吗?据说,中央情报局对谋杀您的事件一点也不感到遗憾。
马:就各种谋杀事件而言,我不相信同美国有关系。事实上,在发生最近一次谋杀事件之前,正是美国驻内罗毕使馆的人员在我访问非洲期间告知我说,我的生命处在危险之中。他们对我说:“我们获悉有人图谋在您回国途中杀害您。您要多加小心。”几天后,在塞浦路斯的人向我证实了这一消息。他们还说,暗杀将在15天之内发生。后来所发生的事情正是这样。至于政变……我不知道。基辛格向我表白说:“发生反对您的那种政变并不符合我们的利益。”我想我理应相信他。但是我应该相信他吗?无数的迹象恰好向我表明事情同基辛格所说的相反,只是我缺乏任何确凿的证据。我还向雅典打听消息,想了解得更多一些,但一切都枉然。我拿不出可以证实我的看法的证据,也就不得不把自己的看法深藏在心中。基辛格说:“当然,我们在注视着形势,我们清楚,约安尼迪斯不喜欢您,军政府的其他人也不喜欢您。但是我们没有获得何日将对您发动政变的具体情报。”
法:也许您7月写给吉齐基斯<small>[5]</small>的一封信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马:我们可以说,那封信加速了政变的发生。但即使不写那封信,政变照样也会在一个月或两个月之后发生。正如基辛格所承认的那样,这是再肯定不过的了:仅仅时间的早晚有待决定而已。在“归并”的分裂活动中,我是最大的障碍。他们热衷于“归并”的活动。每当我们行将达成土耳其族塞浦路斯人和希腊族塞浦路斯人之间的协议时,雅典的军官便高喊“归并”来加以干涉。他们说:“你们当地的协议无关紧要,我们的目标是归并。”我记得,有一天,其中的一名军官前来对我说:“您应该宣布归并,现在离土耳其出兵塞浦路斯还有四五天时间,还来得及,而且到时美国将会进行干预,并阻止他们入侵这个岛屿。在一周之内,归并将成为一个‘既成事实’。”也许他们真的以为让我们合并于希腊的可能性是那样显而易见。然而不管他们如何强求我接受雅典的命令,不管他们如何强求我像傀儡似的听命于他们,就我的秉性而言,这是绝对办不到的。我仅仅听命于自己。
法:那么您也预期必将发生这次军事政变?
马:不,我永远也不相信他们会愚蠢到真的要策划一场反对我的政变。我觉得他们不考虑政变的后果是不可能的。总之,它会引起土耳其的干涉。我相信他们至多也只能做类似同土耳其达成协议这类事,也就是说允许土耳其进行干涉,而希腊则予以还击。这样,分割和双重归并就可以从这里开始。就是在军事政变之后,当我抵达伦敦时,我仍对此深信不疑。我需要时间去证明约安尼迪斯仅仅是因为缺乏明智才这样做的。不过,应该说,我过去就了解他。在1963年和1964年,他作为国民卫队的军官来到塞浦路斯。一天,他在桑普森陪同下来找我,秘密地向我陈述了一项他已经作了部署的计划。他躬着身子,毕恭毕敬地吻我的手说:“宗座,计划在此。在全岛向土耳其族塞浦路斯人发动突然进攻,把他们逐个逐个地全部消灭,这样,问题就解决了。”我惊讶万分,回答他说,我不同意他的计划,我也不能理解这种枉杀无辜群众的邪念。他又吻了吻我的手,怒气冲冲地走了。我告诉您吧,他是个罪人。
法:您觉得帕帕多普洛斯好些吗?
马:我可以说是的。如果我不得不在帕帕多普洛斯和约安尼迪斯之间进行选择的话,那么我将选择前者。至少他更聪明些,或者说是不太愚蠢的人。他在发动军事政变后不久,作为希腊总统府部长到塞浦路斯来时,我首次见到了他。谁也不能说我当时非常看重他。但是我后来前去雅典讨论塞浦路斯问题时,又有两次见到了他。我应该承认,在那两次会晤中,我觉得他是个敏锐的人。不管怎样说,他是个讲究实际的人。是的,帕帕多普洛斯当时妄自尊大,目空一切。此外,我对他在塞浦路斯问题上的真正想法一无所知。但是他有能力同时控制所出现的各种局势。他远比他的同僚高明。我不相信他当初就恨我。他是后来才开始恨我的,是在最近两年中,也许是在最近一年中才开始恨我的。
法:宗座,您也能记恨吗?
马:应该这样说,称之为仇恨的感情是人类天性的组成部分,不能阻止任何人发泄这种可能产生的感情。我不喜欢承认它,因为我是传播博爱的。尽管如此,但有时……有时……好吧,我们可以说,我不太喜欢某些人。您笑什么?
法:因为您使我想起了某些统率军队作战的教皇。我不明白您究竟是个怎样的神甫。我的结论是您根本不是个神甫,而是个穿着神甫衣服的大政治家。
马:您说错了。我首先是个神甫,然后才是个政治家。说得更明确些,我完全不是个政治家,我是个神甫,首先是个神甫,第一是神甫。是一个公众举荐他担任国家元首,从而成为政治家的神甫。但是您内心可能会说您不喜欢这种说法。
法:是的,您使我感到迷惑不解。在我看来,世俗人的斗争恰恰在于不允许神权和世俗权的结合,在于阻止一个宗教领袖同时成为一个政治领袖。
马:而在我看来,这是相当正常的,在塞浦路斯更是如此。因为在那里大主教就像主教一样都是通过全民投票,由人民直接选举出来的。换言之,在塞浦路斯,大主教不仅仅是教会的代表和管理者,而且也是国家的代表,是个总督。在我看来,教会还要关心生活的各个方面:基督教不仅仅局限于关注人类的道德进步,而且还关心人们的社会福利。我看不到我的神甫地位和总统地位之间有什么冲突。我看不到我在掌握神权和世俗权上有什么丑闻。其实,我不依靠某个政党,我不是个靠四处游说争取选票的政党领导人。我用人民的坚执要求和几乎一致的选票所赋予我的两个职务为他们服务。如同多年前我对一个世俗人乔治·帕潘德里欧总理所表白的那样,我之所以强大是因为我软弱。因为我既没有党,也没有军队和警察作为我的后盾。因为我连政治的规律都一窍不通。因为我奉行的原则是基督教的准则,而不是政治手腕、政治花招和政治阴谋。